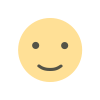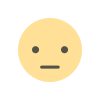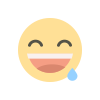歷經無氧、暴風雪...台灣好手攀未知路線,登8千公尺世界第七高峰|天下雜誌
2023年3月,台灣登山家呂忠翰、張元植與隨行紀錄雪羊,一同前往世界第七高峰道拉吉里。長達兩個月的冒險之旅,是台灣人首度嘗試在8,000公尺高峰上自主攀登,高峰冰河上的壯闊、恐懼與驚險,雪羊用文字記錄了下來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2023年5月3日 尼泊爾,道拉吉里基地營,海拔4,670公尺 大雪已經下了三天,每天起床的第一件工作,就是用鏟子把帳篷周遭的積雪鏟開,否則帳篷就會被雪的重量往內擠壓變小,最終崩潰。根據前一天南卡捎來的消息,尼泊爾最近天氣到處都一樣爛,下山看牙齒的卡洛斯再五天才會回來,加德滿都已經連下七天雨了;聖母峰只有架繩隊到第四營,馬卡魯只有架繩隊到第二營,沒人上第三營。由於太多天沒有直升機運補,此刻基地營的有氣飲料已完全斷糧,其他物資也在迅速減少中。 道拉吉里被低壓籠罩,具象與抽象層面都是,本該清澈的空氣因為人們的浮躁,開始變得混濁了起來。 下雪時灰濛濛的天氣,就像攀登者們的心情,歐列格更是毫不掩飾地天天用俄語咒罵著天氣、看著時間表嘆息,這幾乎是他受困基地營的每日例行公事,我聽著聽著都會講幾句了。除了布列德已經決定撤退外,其他營地也開始有人要撤退下山,根據元植的說法,他們大概是把攀登時間表排得太緊,機票改到不能再改的人。 有次夜裡上廁所遇到正在鏟雪的烏塔,連來過三次道拉吉里的她,都說沒看過這種雪量,兩天下一公尺連帳篷都快不見了。「這應該是冬天才會出現的量。」回到帳裡,馬素也無奈地搖著頭說。天氣真的是道拉吉里最不可控的風險,連老手都無法預測。那天睡前正好遇到在餐廳和其他人打牌的巴蒂雅,她說:「我有二十二次8,000米攀登經驗,這是頭一次看到基地營下雪下成這樣,可想而知上面一定更誇張。這雪太可怕,風險太高了,我和模里西奧決定等太陽曬兩、三天,該崩的雪都崩一崩之後再出發。」 我們不約而同看向被基地營燈火照亮的冰河前緣,在它右側往上的路徑早已還原成一個完美的大雪坡,堆著滿滿鬆雪,不知道被推去走第一個開路的雪巴心情會有多糟。 這天下午三點,米高受邀來我們的小餐廳討論攀登策略,眾人分享著米夏早上煮的超辣「卡爾喬」(XapЧo)─一種傳統的喬治亞濃湯料理,是歐列格的家鄉味,但材料從牛肉換成了基地營現有的雞。 「如果5月4日放晴,那要再等兩天,讓新雪崩完我才會安排架繩隊去工作。」「有沒有別的路線可以早一點出發?天氣明明這麼好。」「沒有。」「真的沒有嗎?」「是的。」 此時的歐列格,焦慮與不悅已明明白白寫在臉上,馬素手上拿著他們長長的攀登計畫,上頭畫有密密麻麻的刪改線─原來,他們不只要爬這裡,而是打算在道拉吉里登頂之後,把握身體已完成高度適應的優勢,馬上搭乘直升機飛到世界第五高峰馬卡魯開始攀登。 為了連登這兩座八千米高峰,歐列格已經付出了可能高達五百萬台幣的費用,但眼下他們的預備天幾乎要用完了,這裡的攀登卻依然沒什麼進展。情勢困頓得令人絕望,卻又無可奈何。 就算是富豪,五百萬台幣打水漂也是會心痛的。在商業攀登的世界裡,沒有登頂就是失敗,就是什麼都沒有。這樣的心態在基地營幾乎是共識,但在西北稜的那段日子裡,卻不是這樣。我永遠記得阿果、元植在第二次架繩回來時,那興奮的表情,還有那句「每一步都是在寫歷史」,展現出竭盡自己所有能力嘗試後,所收穫名為「開創」的甜美果實。 歐列格與米高的對話,是被時間表追著跑的當代價值觀,與靠天吃飯、臨機應變不預設明確目標的喜馬拉雅山區自然價值觀之間的強烈碰撞。現代人總是試圖把自己的時間塞滿,努力透過縝密計畫掌控一切,追求「充實與效率」,但往往忽略了順應自然做出反應、保留餘裕的重要性。 此刻,擺在桌上的俄羅斯隊攀登時間表已經比預定計畫大幅延遲。眼看即將壓縮到在預定的5月28日前「爬完道拉吉里與馬卡魯兩座8,000米並返國」的目標,所以才如此著急,天天都想趕快衝上去爬完。相對地,米高與架繩隊並沒有幾月幾號一定要完成什麼事的預定排程表,他們只對自己工作需要的時間有把握:只要六天好天氣就能完成全段架繩,但一切以天氣狀況為基準,天氣不好,就是等待。 這種被大自然決定命運,而不試圖掌控一切的價值觀,是喜馬拉雅山腳千百年來在這片冰雪中打磨出的文化與態度。但我想,這應該同時也是尼泊爾人做事如此不可靠、隨機變化性如此大的原因吧。就算做事隨便敷衍,仍然有人會以「天意」為理由說服自己接受,這樣一來,追求改進與完美就沒那麼重要了。 金錢萬能,但有些東西是花再多錢也買不到的,比如理想的天氣,與按表操課的未來。縱然家財萬貫,請了強力輔助,但山不讓你爬時,無論付出什麼代價都無法改變現實。我想,對一個富豪而言,山這種「無法完全掌控」的特性,或許也在某種程度上,為平常幾乎能掌控人類社會一切元素的他們,帶來了「不可預測的新元素」的樂趣吧。 歐列格這種以直升機單季連爬數座8,000米的風格,也是近十年左右才流行起來而已。一方面是以前爬山的富豪比較少,一方面是商業攀登名人對於「多短時間內完成十四座8,000米」的狂熱追求,帶動了花得起錢的客人群起效尤,讓這本該保有餘裕、順應自然、感受山脈的純粹攀登,染上了倚重金錢、追求效率的社會凡塵。 不過,基地營的攀登者也分成兩大派性格,一種是經驗老到卻不急躁,有目標卻也能接受不確定性的人,如巴蒂雅夫婦、布列德等。長年的攀登經驗,讓他們知道高峰攀登沒有違抗天氣的可能,所以不會一直急著問計畫問進度,而是把自己交給山,讓山來決定自己的去留。 另一種則是目標明確且積極攀登的人,通常也經驗豐富,像波蘭登山家二人組,以及我的好朋友俄羅斯隊。他們有縝密安排的時間表與目標,這一季要攀登的山也不只一座,在巨大的時間壓力下,任何等待與不確定性都是折磨人的浪擲光陰,且可能擠壓到後面的行程,使完整的計畫泡湯。所以他們會非常積極地看天氣,和雪巴確認攀登行程,不斷討論與修改計畫,並假設「如果天氣都在預期之中要做什麼」而顯得焦躁不安,甚至出現像一開始質疑雪巴開路不力的衝突。 兩天後,太陽照進山谷,下了多天的雪終於放晴。基地

2023年3月,台灣登山家呂忠翰、張元植與隨行紀錄雪羊,一同前往世界第七高峰道拉吉里。長達兩個月的冒險之旅,是台灣人首度嘗試在8,000公尺高峰上自主攀登,高峰冰河上的壯闊、恐懼與驚險,雪羊用文字記錄了下來

2023年5月3日
尼泊爾,道拉吉里基地營,海拔4,670公尺
大雪已經下了三天,每天起床的第一件工作,就是用鏟子把帳篷周遭的積雪鏟開,否則帳篷就會被雪的重量往內擠壓變小,最終崩潰。根據前一天南卡捎來的消息,尼泊爾最近天氣到處都一樣爛,下山看牙齒的卡洛斯再五天才會回來,加德滿都已經連下七天雨了;聖母峰只有架繩隊到第四營,馬卡魯只有架繩隊到第二營,沒人上第三營。由於太多天沒有直升機運補,此刻基地營的有氣飲料已完全斷糧,其他物資也在迅速減少中。
道拉吉里被低壓籠罩,具象與抽象層面都是,本該清澈的空氣因為人們的浮躁,開始變得混濁了起來。
下雪時灰濛濛的天氣,就像攀登者們的心情,歐列格更是毫不掩飾地天天用俄語咒罵著天氣、看著時間表嘆息,這幾乎是他受困基地營的每日例行公事,我聽著聽著都會講幾句了。除了布列德已經決定撤退外,其他營地也開始有人要撤退下山,根據元植的說法,他們大概是把攀登時間表排得太緊,機票改到不能再改的人。
有次夜裡上廁所遇到正在鏟雪的烏塔,連來過三次道拉吉里的她,都說沒看過這種雪量,兩天下一公尺連帳篷都快不見了。「這應該是冬天才會出現的量。」回到帳裡,馬素也無奈地搖著頭說。天氣真的是道拉吉里最不可控的風險,連老手都無法預測。那天睡前正好遇到在餐廳和其他人打牌的巴蒂雅,她說:「我有二十二次8,000米攀登經驗,這是頭一次看到基地營下雪下成這樣,可想而知上面一定更誇張。這雪太可怕,風險太高了,我和模里西奧決定等太陽曬兩、三天,該崩的雪都崩一崩之後再出發。」
我們不約而同看向被基地營燈火照亮的冰河前緣,在它右側往上的路徑早已還原成一個完美的大雪坡,堆著滿滿鬆雪,不知道被推去走第一個開路的雪巴心情會有多糟。
這天下午三點,米高受邀來我們的小餐廳討論攀登策略,眾人分享著米夏早上煮的超辣「卡爾喬」(XapЧo)─一種傳統的喬治亞濃湯料理,是歐列格的家鄉味,但材料從牛肉換成了基地營現有的雞。
「如果5月4日放晴,那要再等兩天,讓新雪崩完我才會安排架繩隊去工作。」「有沒有別的路線可以早一點出發?天氣明明這麼好。」「沒有。」「真的沒有嗎?」「是的。」
此時的歐列格,焦慮與不悅已明明白白寫在臉上,馬素手上拿著他們長長的攀登計畫,上頭畫有密密麻麻的刪改線─原來,他們不只要爬這裡,而是打算在道拉吉里登頂之後,把握身體已完成高度適應的優勢,馬上搭乘直升機飛到世界第五高峰馬卡魯開始攀登。
為了連登這兩座八千米高峰,歐列格已經付出了可能高達五百萬台幣的費用,但眼下他們的預備天幾乎要用完了,這裡的攀登卻依然沒什麼進展。情勢困頓得令人絕望,卻又無可奈何。
就算是富豪,五百萬台幣打水漂也是會心痛的。在商業攀登的世界裡,沒有登頂就是失敗,就是什麼都沒有。這樣的心態在基地營幾乎是共識,但在西北稜的那段日子裡,卻不是這樣。我永遠記得阿果、元植在第二次架繩回來時,那興奮的表情,還有那句「每一步都是在寫歷史」,展現出竭盡自己所有能力嘗試後,所收穫名為「開創」的甜美果實。
歐列格與米高的對話,是被時間表追著跑的當代價值觀,與靠天吃飯、臨機應變不預設明確目標的喜馬拉雅山區自然價值觀之間的強烈碰撞。現代人總是試圖把自己的時間塞滿,努力透過縝密計畫掌控一切,追求「充實與效率」,但往往忽略了順應自然做出反應、保留餘裕的重要性。
此刻,擺在桌上的俄羅斯隊攀登時間表已經比預定計畫大幅延遲。眼看即將壓縮到在預定的5月28日前「爬完道拉吉里與馬卡魯兩座8,000米並返國」的目標,所以才如此著急,天天都想趕快衝上去爬完。相對地,米高與架繩隊並沒有幾月幾號一定要完成什麼事的預定排程表,他們只對自己工作需要的時間有把握:只要六天好天氣就能完成全段架繩,但一切以天氣狀況為基準,天氣不好,就是等待。
這種被大自然決定命運,而不試圖掌控一切的價值觀,是喜馬拉雅山腳千百年來在這片冰雪中打磨出的文化與態度。但我想,這應該同時也是尼泊爾人做事如此不可靠、隨機變化性如此大的原因吧。就算做事隨便敷衍,仍然有人會以「天意」為理由說服自己接受,這樣一來,追求改進與完美就沒那麼重要了。
金錢萬能,但有些東西是花再多錢也買不到的,比如理想的天氣,與按表操課的未來。縱然家財萬貫,請了強力輔助,但山不讓你爬時,無論付出什麼代價都無法改變現實。我想,對一個富豪而言,山這種「無法完全掌控」的特性,或許也在某種程度上,為平常幾乎能掌控人類社會一切元素的他們,帶來了「不可預測的新元素」的樂趣吧。
歐列格這種以直升機單季連爬數座8,000米的風格,也是近十年左右才流行起來而已。一方面是以前爬山的富豪比較少,一方面是商業攀登名人對於「多短時間內完成十四座8,000米」的狂熱追求,帶動了花得起錢的客人群起效尤,讓這本該保有餘裕、順應自然、感受山脈的純粹攀登,染上了倚重金錢、追求效率的社會凡塵。
不過,基地營的攀登者也分成兩大派性格,一種是經驗老到卻不急躁,有目標卻也能接受不確定性的人,如巴蒂雅夫婦、布列德等。長年的攀登經驗,讓他們知道高峰攀登沒有違抗天氣的可能,所以不會一直急著問計畫問進度,而是把自己交給山,讓山來決定自己的去留。
另一種則是目標明確且積極攀登的人,通常也經驗豐富,像波蘭登山家二人組,以及我的好朋友俄羅斯隊。他們有縝密安排的時間表與目標,這一季要攀登的山也不只一座,在巨大的時間壓力下,任何等待與不確定性都是折磨人的浪擲光陰,且可能擠壓到後面的行程,使完整的計畫泡湯。所以他們會非常積極地看天氣,和雪巴確認攀登行程,不斷討論與修改計畫,並假設「如果天氣都在預期之中要做什麼」而顯得焦躁不安,甚至出現像一開始質疑雪巴開路不力的衝突。
兩天後,太陽照進山谷,下了多天的雪終於放晴。基地營一掃陰霾,每一頂寢室帳上頭都堆滿準備曬乾的睡墊、睡袋,似乎連飄蕩的五色旗都唱起歌來。我也把握好久不見的太陽,洗了這二十天來的第一次澡,實在是太舒服啦!大基地營的淋浴帳有水袋、水管與小花灑組成的淋浴系統,熱水的量也多了不少,比日本營要來得高級些。
這天稍晚,不只直升機載來了從安娜普納過來的攀登者,來自挪威的薇比(Vibi)與巴基斯坦的年輕登山家什羅澤.卡西夫(Shehroze Kashif,世界上最年輕的K2登頂者),連阿果、元植也在稍晚抵達了基地營。
「哇,阿果、元植!你們來了!」
「羊羊!你過得還好嗎?」
看到彼此的瞬間,我們三人激動得抱在一起,嘰哩呱啦地互相吐槽前幾天的風雪有多災難。不只我們這邊開路不順利,只有兩人的他們在西北稜的攀登也是吃盡苦頭,好不容易才又多往前推進了一些,就回日本營避難了,下降過程中甚至差點掉進冰隙。這時的日本營也很慘,幾乎斷糧,只剩七顆蛋、一點罐頭、馬鈴薯,所有的肉已經吃完,再不上來拿東西就真的要吃土了。
阿果一到基地營,依然像明星般受到各路人馬歡迎,不只攀登者認識至少一半,雪巴嚮導、員工們也認識不少,光是串門子聊天就耗去大把時間。元植說,其實8,000米攀登者就是一批一批的,離開馬納斯盧、聖母峰後,很容易就遇到曾一起攀登的人。常有人說山岳界很小,但以這個狀況來看,8,000米的攀登更是世界尺度的小。
阿果、元植來基地營的隔天,俄羅斯隊開了一個漫長沉重的會議。南卡說架繩隊看起來三天後才能到第一營,再兩天到第二營,然後回來伺機而動。歐列格臉色非常難看地爆出一連串髒話,若是真等他們架好路,馬卡魯就徹底不用爬了,那將是上百萬的損失。馬素參考了天氣預報後,決定兩天後就出發攀登,到第一營長駐伺機而動,一直待到可以衝頂(Summit Push)就衝。山頂可能有時速近百公里的強風預報就先不管了,反正第一營避風,且戰且走。
或許是我們即將出發的消息不脛而走,到了下午,整個基地營在陽光下充滿了即將戰鬥的氛圍,沒有一個攀登者兩天後不一起出發的,有種總動員之感。
這時,我也終於見到了我的雪巴嚮導:拉卡帕(Lakpa Sherpa),名字是「禮拜四」的意思。雪巴文化喜歡用出生的日子為孩子命名,所以一週七天的名字十分常見,像基地營的達瓦就有兩個,拉卡帕也是。他的臉型渾圓,黝黑的面容搭配環繞嘴唇一圈的鬍子,話不是很多,感覺挺穩重。阿果和薩加都說他在這裡算專業的,而且剛從安娜普納下來,高度適應很好,令我安心不少。
5月8日凌晨4:45,背著七天份的乾燥糧食,我們踏著堅定的步伐,再次走向那時時雪崩的大山壁,朝著世界第七之巔進發。
(本文摘自高寶出版《道拉吉里的風》)
你的反應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