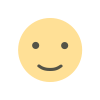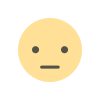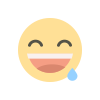連結台灣與沖繩的公民課——專訪沖繩反自衛隊基地運動領袖宮良麻奈美
沖繩反軍事和平運動新一代領袖宮良麻奈美受訪照。 圖/陳志剛攝影 寫在專訪之前 5月賴清德總統就職時,日本國會共有三十餘名跨黨派參眾議員來臺表達祝賀。一同從日本前來的,還有沖繩縣石垣市的市長中山義隆。他5月19日在X上的推文寫到「臺灣是世界承認的國家」、「祝賀朋友臺灣」,被臺灣媒體視為溫暖的祝福。 不過,石垣市長的對臺祝賀,卻在沖繩內部掀起討論與質疑。當地報紙《沖繩時報》便認為石垣市長的發言與日本政府的政策不符,擔憂這可能會引起中國的反彈。 其實,在這種爭論背後,存在著沖繩社會對於沖繩可能捲入臺海戰事的擔憂。近10年來,日本政府為了對應中國與北韓對區域秩序的挑戰,著手將國防重心調整到以琉球列島為主的南西諸島(即琉球群島),並在過去未派駐自衛隊的石垣島、宮古島、與那國島等島嶼,興建了設有飛彈部隊的軍事基地。對此,有些沖繩民眾認為這將嚇阻中國繼續擴大軍事勢力,但也有人擔憂這將導致沖繩再次陷入戰火。 筆者平時居於日本,以臺灣和沖繩為中心進行東亞近現代史的研究。這幾年觀察沖繩與臺灣的輿論時,發現支持加強戰備力量的臺灣知識份子,與主張撤除軍事基地的沖繩意見領袖之間,基於立場差異時常出現齟齬。由於公民社會通常扮演社會上良善的力量,筆者看到上述臺沖兩地公民社會的溫差與對立,不禁感到頗為可惜。 就在這時,筆者讀到了《報導者》在2023年對於沖繩反戰人士的專訪。報導中來自石垣島的宮良麻奈美小姐,她期盼加深臺灣與沖繩之間的相互理解,重建彼此關係的想法,吸引了筆者的目光。這似乎是重新銜接臺沖兩地公民社會的鑰匙。 為此,筆者在2024年5月前往石垣島訪問宮良小姐。交談之中得知,宮良小姐其實跟大多數人一樣,並非天生的社運參與者,而是有感於故鄉環境遭遇挑戰,才選擇走上街頭,意圖守護自己的家鄉。而這些行動的根底,除了是拒絕軍事手段之外,同時有著對於自由、民主與自決權的想望。 經宮良小姐的慷慨同意,筆者將我們之間的對談整理成文字。藉由宮良小姐第一人稱敘述,期待可以讓臺灣讀者更具體地理解,何以有些沖繩的年輕人會選擇走上街頭,並感受到筆者訪談過後的感觸:「我們都是活生生的人,而我們沒有那麼不一樣」。 圖:日本石垣島的陸上自衛隊基地。 圖/路透社 訪談時間:2024年5月13日 受訪者:宮良麻奈美 訪談者:陳志剛 訪談地:日本沖繩縣石垣市 (訪談正文) 陳:宮良小姐您好,我是來自臺灣的陳志剛,很榮幸有機會訪問您。 宮良:我是石垣島出身的宮良麻奈美。我在1992年出生,今年31歲。我到高中畢業為止都在石垣島就學,在東京取得學士學位後,2018年回到石垣島。那一年,由於石垣市政府突然批准自衛隊在島上開設基地,我與許多不滿的市民發起行動,要求市政府依法舉行與此相關的公民投票,以凸顯民意對軍事基地的想法。 陳:關於這點,您2023年於《報導者》的專訪上曾經說明要求舉行公投的運動過程。誠然,自衛隊基地是促使您走上街頭的直接原因。不過據說也與您的成長過程和家庭背景有關。能否請您跟我們分享呢? 宮良:我的祖父與曾祖父都與戰爭有直接關聯。我的祖父在十幾、二十幾歲時被徵召前往海外戰鬥。據說祖父因為眼睛比較大,因此被指派觀測敵軍飛機的任務。讓我印象深刻的是,祖父曾說自己從軍時每天都有同袍死去,到後來已經習慣身邊都是屍體的情況了。當時祖父常常想著,自己或許明天就會戰死,對死亡已經感到麻痺,不會感到害怕了。 另一方面,我的曾祖父則在戰爭末期搭上了從石垣島撤退往臺灣的船隻。然而,船隻在航行途中遭到美軍攻擊,船隻喪失動力並漂流到尖閣諸島,也就是釣魚臺。這在日本被稱為「尖閣諸島戰時遭難事件」。許多漂流到釣魚臺的人們,因為缺乏食物與乾淨飲用水而喪失了性命。我的曾祖父也是其中一人。為了不要忘記在戰爭中過世的人們,石垣島至今依然存在著相關的遺族會,每年舉行慰靈儀式。這與政治上的意識形態無關,純粹只是希望想撫慰這些人的靈魂而已。 至於我自己,學校教育也對我的戰爭觀造成了影響。小學時期,學校的教育內容包括所謂「和平教育」,每年都會觀看與戰爭有關的動畫與戲劇,藉此了解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災難。課堂上提到在二戰末期的沖繩,包括沖繩與日本本土的人們都被要求為了天皇犧牲性命,而比起被敵軍俘虜,還不如跳下懸崖、集體自殺。課堂之外,小學六年級時會舉行學習發表會,演出與戰爭有關的戲劇。當時我在以八重山為背景的戲劇裡飾演軍人的角色。藉由演出加害者而非被害者的角色,這讓我可以更多面地理解戰爭。這可以說是我從事運動的背景吧。 藉由祖父與曾祖父的經驗,再加上學校裡和平教育的影響,我不禁感到「並非只有『敵人』才是敵人」的道理。只要是軍事力量,就算是「友軍」,也會在戰爭時期對平民造成威脅。也因此,即使到了現在,雖然自衛隊在日本本土常被認為是保護國家與領土的存在,但是沖繩的人們恐怕還是會將自衛隊與過往戰爭的記憶予以疊合。也就是說,今日沖繩的和平與反基地運動,雖說直接起因於當今局勢,但背後其實也受到每個家庭在戰爭時期的經驗影響。 日本陸上自衛隊部署於石垣島的愛國者三型飛彈。 圖/路透社 陳:您的家人在戰爭時有過艱難的經驗,而您也在學校接受了和戰爭與和平有關的教育。這些都是您日後開始參加運動的基礎。不過,即使有這樣的背景,沒有人一開始就是社會運動者,大家一開始都可以說是政治素人。對宮良小姐來說,促使您直接投身運動的仍然是2018年前後的。能否請您分享您從政治素人變成社會運動、反基地運動參與者的經緯呢? 宮良:我其實一開始並不是對政治有熱情的人。我頂多會在選舉時去投票,但也沒有參與過選舉相關的活動。我還在東京讀大學時,當時東京幾乎沒有報導石垣島即將興建軍事基地的新聞,只有一兩行的網路新聞提到這件事。我當時覺得自衛隊基地就像警察署或消防局一樣,並不特別值得關注或討論。 與東京的狀況相比,我是在回到石垣島後才發現事情的嚴重性。當時石垣島正在進行市長選舉,自衛隊基地興建問題成為選舉的焦點。當時其他島民跟我說,自衛隊基地即將蓋在於茂登山的山麓。這讓我大感訝異。在石垣島有許多的「御嶽」,我們會在那裡進行祈禱。於茂登山可以說是石垣島信仰的核心,山本身就是信仰的對象。此外,於茂登山也是石垣島自然生態系的中心,也提供了農業與生活用水。由於沖繩島已經發生了基地導致水質污染的情況,石垣島的人們自然會對於在此地興建自衛隊基地感到懷疑。這是讓我們覺得應該對此進行公民投票的原因。 當然,只有我自己一個人是無法辦到的。即使想成立組織也非易事。這時,我受到沖繩島的人們的啟發。在沖繩島,當局為了興建新的美軍基地,正在「邊野古」這個地方進行填海造陸工程。對此,以二十幾歲的年輕人為中心,沖繩的人們發起了要求舉行公民投票的運動。看到他們的行動,我感到石垣島的年輕人也許也可以嘗試看看這個方法。換句話說,沖繩島人們的行動給予了我們很大的勇氣。 回到石垣島,為了推動公民投票,我們並非隨意做做問卷而已,而是依據法規,將民眾的連署提交給選舉管理委員會,再提交給市長,以舉行公民投票。法規要求要有四分之一選民的連署,我們則在一個月內收集到三分之一的連署。我們當時認為,這樣應該可以進行公投了吧。然而市長依然不願意舉行公投,而是聽從國家的指示繼續進行基地建設。在公民投票未能實施的狀況下,石垣島的自衛隊基地在2023年落成。 面對這個狀況,我不禁感到,如果不能保護當地居民的生活,如果不尊重當地的民意,那國防、安全保障還有什麼意義呢? 這也讓我想到,沖繩之所以會有這麼多美軍基地,其實是在戰後初期,日本本土的美軍基地在當地人反對之下轉移到沖繩。當時美軍強制徵收了沖繩人民的土地。軍隊拿著槍枝,駕著推土機把沖繩居民的住宅剷平。這被稱為「槍劍與推土機」。這些失去家園的沖繩人之中,有不少人來到了石垣島,落腳在於茂登山周圍,進行農業開墾。然而數十年過後,他們好不容易落地生根,生活又再次受到自衛隊基地帶來的威脅。 我認為,軍隊帶來的傷害一直以各種形式、作用於沖繩的各個角落。看看過去的歷史,我不禁懷疑這幾十年有任何好轉。即使沖繩已經「回歸」日本五十年,日本政府與日本國民都表示應該減少沖繩的軍事基地,但實際看看現況,基地根本沒有減少,反倒是增加了。這是把我們推向街頭的根本原因。我們並不是為了某種理念或正義,而是基於自己的生活經驗,對於現狀感到不安,才選擇站出來進行運動的。 沖繩民眾俯望美軍普天間基地。 圖/美聯社 陳:接著想請問您在從事運動的過程中,曾經感受到壓力嗎?您與家人或朋友的關係是否受到影響?此外,是否有哪些瞬間曾讓你感到「幸好有參加這場運動」? 宮良:最一開始,我當然是滿害怕參加運動的。由於要在不熟悉的媒體前露臉,談論的議題也相當敏感,即使害怕也得裝作不害怕,起初的確感到很大的壓力⋯⋯雖然現在我已經習慣了(笑)。 很幸運的是,我周遭人們的反應比我最初想像的好許多。家人們一開始對我從事運動感到相當擔心。其他朋友們也常對我說:「最後受傷的會是你自己喔」、「跟國家作對也沒用的吧」、「成熟一點吧」。不過從開始從事運動至今過了六年,家人與朋友們則變得相當支持我,也很訝異我可以持續參加運動到現在。 同時我也感受到,石垣島內的年輕世代開始以不帶偏見的積極態度對待運動。在此之前,在日本進行運動時常遭到別人冷眼相待,但這不是正常民主國家該有的現象。我開始從事運動以後,也有朋友開始因此對議題感興趣。人們開始意識到運動與議題並非遙遠的存在,而是正發生在自己周遭的事情。 2024年5月美國駐日大使Rahm Emanuel造訪石垣市,反對自衛隊基地的民眾舉牌抗議。 圖/美聯社 另一方面,意想不到的是,從事運動也替我帶來與他人的豐富連結。雖然自衛隊基地已經落成,而公民投票也並未實施,但藉由參與運動,我認識了許多抱持共通想法的日本本土朋友。我們共享著「因為是民主國家,更要珍惜民主制度」的想法。為此,我們也向拒絕實施公投的市長提起訴訟,現在正在進行著。 這種連結不僅限於日本國內。參與運動以降,我開始與臺灣的人們、其他國家的人們有了交流。雖然我們在討論的過程中,在軍備、國防上會有著不同意見,但我們也感受到,彼此在最根本的民主、自由、自決權的價值觀上是一致的。藉由與這些人產生連結,我跨越了國境的限制,視野也變得更加寬闊。為此,我很慶幸自己參加了這場運動。 陳:你提到了與臺灣的人們交流。這讓我想到2023年曾經舉行名為「沖臺對話」的座談會,以及該活動引起的後續討論與爭論。關於這點,能否請宮良小姐向我們分享您對沖臺交流的想法呢?又或者說,您覺得什麼才是真正的互相理解呢? 宮良:我可以理解,我也想要理解,臺灣人在當前國際環境下追求武力、追求與美日加強合作的想法。與此同時,我們在沖繩則是追求沖繩自己的自立、自決權與自由。但是我們拒絕軍隊、拒絕基地。 乍看之下臺灣與沖繩的訴求有所不同,好像難以一起攜手前進。然而,我覺得我們其實在根本上共享一樣的價值觀。我們雙方都追求著自由、民主與自決權。但在我的想法裡,我覺得如果我們持續身陷大國之間的權力遊戲,那臺灣與沖繩將擺脫不了棋子的命運。因此,我想試著想像一種不同於大國邏輯的可能性。也就是由臺灣與沖繩一起尋找、創造屬於自己的價值觀。所以,雖然我們之間也許會有意見衝突之處,但我還是想好好理解臺灣人的想法與立場,與此同時,我也希望被你們理解。此後我希望可以繼續進行沖繩與臺灣之間的交流與對話。 陳:除了與臺灣的交流之外,請問您在未來還有哪些目標呢? 宮良:其實比起從事政治與社會運動,我更想把八重山的歷史與文化傳承給下一世代。這原本應該是我人生的主旋律。然而不管怎麼做,都還是繞不開軍事基地的問題。這不僅僅是我自己面對的問題。在沖繩,無論是文化活動或是經濟活動,無論想做什麼事,到最後幾乎都會與基地的問題扯上關係,而這會耗費我們不少精神與力氣,有時甚至讓我們不能從事自己原本想做的事情。也就是說,基地帶來的問題不僅僅是肉眼可見的演習事故或是環境破壞,還包括影響著所有居住在基地之島上人們的人生。這是外人難以輕易察覺,但對於當地人相當深刻的問題。 回到我自己,我當然有時會覺得累了,不


寫在專訪之前
5月賴清德總統就職時,日本國會共有三十餘名跨黨派參眾議員來臺表達祝賀。一同從日本前來的,還有沖繩縣石垣市的市長中山義隆。他5月19日在X上的推文寫到「臺灣是世界承認的國家」、「祝賀朋友臺灣」,被臺灣媒體視為溫暖的祝福。
不過,石垣市長的對臺祝賀,卻在沖繩內部掀起討論與質疑。當地報紙《沖繩時報》便認為石垣市長的發言與日本政府的政策不符,擔憂這可能會引起中國的反彈。
其實,在這種爭論背後,存在著沖繩社會對於沖繩可能捲入臺海戰事的擔憂。近10年來,日本政府為了對應中國與北韓對區域秩序的挑戰,著手將國防重心調整到以琉球列島為主的南西諸島(即琉球群島),並在過去未派駐自衛隊的石垣島、宮古島、與那國島等島嶼,興建了設有飛彈部隊的軍事基地。對此,有些沖繩民眾認為這將嚇阻中國繼續擴大軍事勢力,但也有人擔憂這將導致沖繩再次陷入戰火。
筆者平時居於日本,以臺灣和沖繩為中心進行東亞近現代史的研究。這幾年觀察沖繩與臺灣的輿論時,發現支持加強戰備力量的臺灣知識份子,與主張撤除軍事基地的沖繩意見領袖之間,基於立場差異時常出現齟齬。由於公民社會通常扮演社會上良善的力量,筆者看到上述臺沖兩地公民社會的溫差與對立,不禁感到頗為可惜。
就在這時,筆者讀到了《報導者》在2023年對於沖繩反戰人士的專訪。報導中來自石垣島的宮良麻奈美小姐,她期盼加深臺灣與沖繩之間的相互理解,重建彼此關係的想法,吸引了筆者的目光。這似乎是重新銜接臺沖兩地公民社會的鑰匙。
為此,筆者在2024年5月前往石垣島訪問宮良小姐。交談之中得知,宮良小姐其實跟大多數人一樣,並非天生的社運參與者,而是有感於故鄉環境遭遇挑戰,才選擇走上街頭,意圖守護自己的家鄉。而這些行動的根底,除了是拒絕軍事手段之外,同時有著對於自由、民主與自決權的想望。
經宮良小姐的慷慨同意,筆者將我們之間的對談整理成文字。藉由宮良小姐第一人稱敘述,期待可以讓臺灣讀者更具體地理解,何以有些沖繩的年輕人會選擇走上街頭,並感受到筆者訪談過後的感觸:「我們都是活生生的人,而我們沒有那麼不一樣」。

訪談時間:2024年5月13日
受訪者:宮良麻奈美
訪談者:陳志剛
訪談地:日本沖繩縣石垣市
(訪談正文)
陳:宮良小姐您好,我是來自臺灣的陳志剛,很榮幸有機會訪問您。
宮良:我是石垣島出身的宮良麻奈美。我在1992年出生,今年31歲。我到高中畢業為止都在石垣島就學,在東京取得學士學位後,2018年回到石垣島。那一年,由於石垣市政府突然批准自衛隊在島上開設基地,我與許多不滿的市民發起行動,要求市政府依法舉行與此相關的公民投票,以凸顯民意對軍事基地的想法。
陳:關於這點,您2023年於《報導者》的專訪上曾經說明要求舉行公投的運動過程。誠然,自衛隊基地是促使您走上街頭的直接原因。不過據說也與您的成長過程和家庭背景有關。能否請您跟我們分享呢?
宮良:我的祖父與曾祖父都與戰爭有直接關聯。我的祖父在十幾、二十幾歲時被徵召前往海外戰鬥。據說祖父因為眼睛比較大,因此被指派觀測敵軍飛機的任務。讓我印象深刻的是,祖父曾說自己從軍時每天都有同袍死去,到後來已經習慣身邊都是屍體的情況了。當時祖父常常想著,自己或許明天就會戰死,對死亡已經感到麻痺,不會感到害怕了。
另一方面,我的曾祖父則在戰爭末期搭上了從石垣島撤退往臺灣的船隻。然而,船隻在航行途中遭到美軍攻擊,船隻喪失動力並漂流到尖閣諸島,也就是釣魚臺。這在日本被稱為「尖閣諸島戰時遭難事件」。許多漂流到釣魚臺的人們,因為缺乏食物與乾淨飲用水而喪失了性命。我的曾祖父也是其中一人。為了不要忘記在戰爭中過世的人們,石垣島至今依然存在著相關的遺族會,每年舉行慰靈儀式。這與政治上的意識形態無關,純粹只是希望想撫慰這些人的靈魂而已。
至於我自己,學校教育也對我的戰爭觀造成了影響。小學時期,學校的教育內容包括所謂「和平教育」,每年都會觀看與戰爭有關的動畫與戲劇,藉此了解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災難。課堂上提到在二戰末期的沖繩,包括沖繩與日本本土的人們都被要求為了天皇犧牲性命,而比起被敵軍俘虜,還不如跳下懸崖、集體自殺。課堂之外,小學六年級時會舉行學習發表會,演出與戰爭有關的戲劇。當時我在以八重山為背景的戲劇裡飾演軍人的角色。藉由演出加害者而非被害者的角色,這讓我可以更多面地理解戰爭。這可以說是我從事運動的背景吧。
藉由祖父與曾祖父的經驗,再加上學校裡和平教育的影響,我不禁感到「並非只有『敵人』才是敵人」的道理。只要是軍事力量,就算是「友軍」,也會在戰爭時期對平民造成威脅。也因此,即使到了現在,雖然自衛隊在日本本土常被認為是保護國家與領土的存在,但是沖繩的人們恐怕還是會將自衛隊與過往戰爭的記憶予以疊合。也就是說,今日沖繩的和平與反基地運動,雖說直接起因於當今局勢,但背後其實也受到每個家庭在戰爭時期的經驗影響。

陳:您的家人在戰爭時有過艱難的經驗,而您也在學校接受了和戰爭與和平有關的教育。這些都是您日後開始參加運動的基礎。不過,即使有這樣的背景,沒有人一開始就是社會運動者,大家一開始都可以說是政治素人。對宮良小姐來說,促使您直接投身運動的仍然是2018年前後的。能否請您分享您從政治素人變成社會運動、反基地運動參與者的經緯呢?
宮良:我其實一開始並不是對政治有熱情的人。我頂多會在選舉時去投票,但也沒有參與過選舉相關的活動。我還在東京讀大學時,當時東京幾乎沒有報導石垣島即將興建軍事基地的新聞,只有一兩行的網路新聞提到這件事。我當時覺得自衛隊基地就像警察署或消防局一樣,並不特別值得關注或討論。
與東京的狀況相比,我是在回到石垣島後才發現事情的嚴重性。當時石垣島正在進行市長選舉,自衛隊基地興建問題成為選舉的焦點。當時其他島民跟我說,自衛隊基地即將蓋在於茂登山的山麓。這讓我大感訝異。在石垣島有許多的「御嶽」,我們會在那裡進行祈禱。於茂登山可以說是石垣島信仰的核心,山本身就是信仰的對象。此外,於茂登山也是石垣島自然生態系的中心,也提供了農業與生活用水。由於沖繩島已經發生了基地導致水質污染的情況,石垣島的人們自然會對於在此地興建自衛隊基地感到懷疑。這是讓我們覺得應該對此進行公民投票的原因。
當然,只有我自己一個人是無法辦到的。即使想成立組織也非易事。這時,我受到沖繩島的人們的啟發。在沖繩島,當局為了興建新的美軍基地,正在「邊野古」這個地方進行填海造陸工程。對此,以二十幾歲的年輕人為中心,沖繩的人們發起了要求舉行公民投票的運動。看到他們的行動,我感到石垣島的年輕人也許也可以嘗試看看這個方法。換句話說,沖繩島人們的行動給予了我們很大的勇氣。
回到石垣島,為了推動公民投票,我們並非隨意做做問卷而已,而是依據法規,將民眾的連署提交給選舉管理委員會,再提交給市長,以舉行公民投票。法規要求要有四分之一選民的連署,我們則在一個月內收集到三分之一的連署。我們當時認為,這樣應該可以進行公投了吧。然而市長依然不願意舉行公投,而是聽從國家的指示繼續進行基地建設。在公民投票未能實施的狀況下,石垣島的自衛隊基地在2023年落成。
面對這個狀況,我不禁感到,如果不能保護當地居民的生活,如果不尊重當地的民意,那國防、安全保障還有什麼意義呢?
這也讓我想到,沖繩之所以會有這麼多美軍基地,其實是在戰後初期,日本本土的美軍基地在當地人反對之下轉移到沖繩。當時美軍強制徵收了沖繩人民的土地。軍隊拿著槍枝,駕著推土機把沖繩居民的住宅剷平。這被稱為「槍劍與推土機」。這些失去家園的沖繩人之中,有不少人來到了石垣島,落腳在於茂登山周圍,進行農業開墾。然而數十年過後,他們好不容易落地生根,生活又再次受到自衛隊基地帶來的威脅。
我認為,軍隊帶來的傷害一直以各種形式、作用於沖繩的各個角落。看看過去的歷史,我不禁懷疑這幾十年有任何好轉。即使沖繩已經「回歸」日本五十年,日本政府與日本國民都表示應該減少沖繩的軍事基地,但實際看看現況,基地根本沒有減少,反倒是增加了。這是把我們推向街頭的根本原因。我們並不是為了某種理念或正義,而是基於自己的生活經驗,對於現狀感到不安,才選擇站出來進行運動的。

陳:接著想請問您在從事運動的過程中,曾經感受到壓力嗎?您與家人或朋友的關係是否受到影響?此外,是否有哪些瞬間曾讓你感到「幸好有參加這場運動」?
宮良:最一開始,我當然是滿害怕參加運動的。由於要在不熟悉的媒體前露臉,談論的議題也相當敏感,即使害怕也得裝作不害怕,起初的確感到很大的壓力⋯⋯雖然現在我已經習慣了(笑)。
很幸運的是,我周遭人們的反應比我最初想像的好許多。家人們一開始對我從事運動感到相當擔心。其他朋友們也常對我說:「最後受傷的會是你自己喔」、「跟國家作對也沒用的吧」、「成熟一點吧」。不過從開始從事運動至今過了六年,家人與朋友們則變得相當支持我,也很訝異我可以持續參加運動到現在。
同時我也感受到,石垣島內的年輕世代開始以不帶偏見的積極態度對待運動。在此之前,在日本進行運動時常遭到別人冷眼相待,但這不是正常民主國家該有的現象。我開始從事運動以後,也有朋友開始因此對議題感興趣。人們開始意識到運動與議題並非遙遠的存在,而是正發生在自己周遭的事情。

另一方面,意想不到的是,從事運動也替我帶來與他人的豐富連結。雖然自衛隊基地已經落成,而公民投票也並未實施,但藉由參與運動,我認識了許多抱持共通想法的日本本土朋友。我們共享著「因為是民主國家,更要珍惜民主制度」的想法。為此,我們也向拒絕實施公投的市長提起訴訟,現在正在進行著。
這種連結不僅限於日本國內。參與運動以降,我開始與臺灣的人們、其他國家的人們有了交流。雖然我們在討論的過程中,在軍備、國防上會有著不同意見,但我們也感受到,彼此在最根本的民主、自由、自決權的價值觀上是一致的。藉由與這些人產生連結,我跨越了國境的限制,視野也變得更加寬闊。為此,我很慶幸自己參加了這場運動。
陳:你提到了與臺灣的人們交流。這讓我想到2023年曾經舉行名為「沖臺對話」的座談會,以及該活動引起的後續討論與爭論。關於這點,能否請宮良小姐向我們分享您對沖臺交流的想法呢?又或者說,您覺得什麼才是真正的互相理解呢?
宮良:我可以理解,我也想要理解,臺灣人在當前國際環境下追求武力、追求與美日加強合作的想法。與此同時,我們在沖繩則是追求沖繩自己的自立、自決權與自由。但是我們拒絕軍隊、拒絕基地。
乍看之下臺灣與沖繩的訴求有所不同,好像難以一起攜手前進。然而,我覺得我們其實在根本上共享一樣的價值觀。我們雙方都追求著自由、民主與自決權。但在我的想法裡,我覺得如果我們持續身陷大國之間的權力遊戲,那臺灣與沖繩將擺脫不了棋子的命運。因此,我想試著想像一種不同於大國邏輯的可能性。也就是由臺灣與沖繩一起尋找、創造屬於自己的價值觀。所以,雖然我們之間也許會有意見衝突之處,但我還是想好好理解臺灣人的想法與立場,與此同時,我也希望被你們理解。此後我希望可以繼續進行沖繩與臺灣之間的交流與對話。
陳:除了與臺灣的交流之外,請問您在未來還有哪些目標呢?
宮良:其實比起從事政治與社會運動,我更想把八重山的歷史與文化傳承給下一世代。這原本應該是我人生的主旋律。然而不管怎麼做,都還是繞不開軍事基地的問題。這不僅僅是我自己面對的問題。在沖繩,無論是文化活動或是經濟活動,無論想做什麼事,到最後幾乎都會與基地的問題扯上關係,而這會耗費我們不少精神與力氣,有時甚至讓我們不能從事自己原本想做的事情。也就是說,基地帶來的問題不僅僅是肉眼可見的演習事故或是環境破壞,還包括影響著所有居住在基地之島上人們的人生。這是外人難以輕易察覺,但對於當地人相當深刻的問題。
回到我自己,我當然有時會覺得累了,不想再繼續從事政治與社會運動了。然而,正是因為我已經知道了現狀,我不能假裝自己不知道而盲目度日。我在今後也想繼續保持著與日本本土的人們,以及臺灣的人們的聯繫。我想與他們進行有關音樂、文學、歷史的文化交流。比方說,八重山在歷史上與臺灣有著許多密切的連結,八重山本身就有不少來自臺灣的移民,我未來會想在這點上多多發展。
由於沖繩在戰爭時期幾乎失去了所有的文化資產,我們今天也會恐懼於可能失去現在所擁有的一切。為了保護我們沖繩的歷史與認同,為了下一個世代,我想盡力於保存文化、學習並傳承歷史的事業。(完)

責任編輯/王穎芝
你的反應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