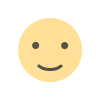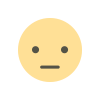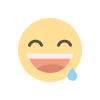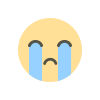全球伦理圆桌会议暨第二届全球伦理国际论坛在罗马成功举办
2024年8月5日,全球伦理圆桌会议暨第二届全球伦理国际论坛在意大利罗马大学顺利举行。论坛以“全球危机之下,如何重启全球伦理?”(Global Ethics: How to relaunch this discussion in the face of global crises?)为主题,作为第25届世界哲学大会“跨越边界的哲学”( Philosophy across Boundaries)圆桌会议之一。复旦大学全球伦理研究中心委员会成员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一同参与了讨论。与会者有复旦大学全球伦理研究中心主任邓安庆教授,复旦大学全球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王金林教授,复旦大学全球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汪行福教授,复旦大学全球伦理研究中心秘书长钱康青年副研究员,复旦大学全球伦理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成员、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Jon Mandle教授,特邀嘉宾同济大学张念教授,以及国内外对全球伦理怀以兴趣、抱以关切的来自诸多国家的学者们。会议分为上下两个半场,每个半场由专题研讨和自由讨论构成。与会学者合影在开场环节,复旦大学全球伦理中心秘书长钱康青年副研究员对复旦大学全球伦理研究中心(后文简称“中心”)的宗旨、性质与架构进行了介绍。他强调,中心旨在基于全球社会面临的伦理挑战,在哲学的层面上深入全球伦理的理论基础,探讨全球伦理的普遍原则与理性根据。鉴于过去数十年来全球伦理在推进和发展的过程中所遭遇到的阻力,中心的创立者们深刻意识到,要想在尊重世界文化多元性的情况下具体地确定某种全球性的伦理规则是及其困难的。因此中心更多的地将自己的定位视为是对全球伦理的理论基础进行深入反思,并且搭建能够促进世界各地的哲学家展开相互对话和交流的平台。经由去年在上海举办的第一届全球伦理国际会议,中心得到了国际学者的大力支持,其中包括来自世界哲学大会主席卢卡教授的认可,并受邀来到罗马参加世界哲学大会并主持全球伦理分会场。作为伦理学和哲学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和合作研究的平台,中心希望打破国界与学科的隔阂,将伦理议题拓展至全球范围,邀请更多学者重启全球伦理的讨论。在上半场会议的专题研讨部分共有三位学者进行了主题报告。第一位报告人是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的Jon Mandle教授,他从哲学的方法论出发对全球伦理的讨论进行了反思。他指出,目前存在两种广为接受的伦理学研究方式:一种可以被称为道德人类学路径,采取这一路径的学者重视实践形态与道德原则的多样性,他们试图对世界各地不同社会、不同社区、不同文化中的道德进行描述;另一种则被归于规范理论,采取这一路径的学者旨在确立合理的道德原则,认为普遍的道德原则可以应用于不同的文化群体,乃至推广至全球范围。但是,这两种研究路径都存在理论上的风险:道德人类学无法从现存的事实出发推导出道德性的规范原则,因而反有可能为特定社会中存在的不公辩护;而规范理论家则忽视了不同社会、文化和群体分享着彼此差异与多样的价值,为了高度抽象的概念与理论牺牲了生活经验的复杂性。Mandle教授指出,道德人类学家和规范理论家需要相互学习,尤其是对于采取后一路径而哲学家而言,应当基于人类学对现实社会的经验考察,以使得诸如自由与平等的抽象概念获得具体的内容。在会议结束后,Mandle教授接受了中的采访,并进一步补充了自己的观点:首先,Mandle教授肯定了1993年《全球伦理宣言》的积极价值。他认为,《宣言》代表着建立一个共享的、全球性的伦理规范的努力,这有助于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相互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信任和熟悉度。尽管在过去、现在和将来,想要形成这样一种全球性的共识都不可避免地会早遇到各种冲突和分歧,但至少大家可以在一种共同推进的努力中探索可以分享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的领域。换言之,即便这种探索无法即刻产生实际的影响,但从长远的视角看,一定是能够对全球伦理的工作产生助益的。接着,Mandle教授指出了重建全球伦理的两重挑战:第一,理论困难,即在承认多样性的前提之下如何构建共同价值观与共同的规范原则;第二,现实障碍,即由于当下广泛存在的信任危机,跨国联结变得困难。哲学家更多考虑的是第一点,也就是探寻普遍的规范原则。然而,单纯对不同的观点进行分类,然后试图找到共识或重叠是不可行的,因为全球性的伦理规范需要被建构而非单纯地被发现。换言之,Mandle教授并不认为有一个全球性的道德规范等待被发现,全球伦理研究的方法应该是一种能够包容和尊重多元价值的哲学重构。所以,解决理论困境的正确途径是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促进不同传统之间的对话。在这个意义上,建构全球伦理的关键在于在统一中保持多样性,在以相互尊重为前提的对话中看到其他观点的合法性,一方面坚持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在与他人的互动中的跨越自身主观性的限制。随后,Mandle教授强调共同原则的合法性在于理性的公共使用,即承认不同观点的平等合法性,并允许这些彼此相异的特定视角与价值被纳入共享视角的构建中。在这种建构中,类似于罗尔斯所提出的“理性的公共使用”是至关重要的。最后,他对复旦大学全球伦理研究中心表达了赞许,认为中心使得世界各地的学者们可以从不同的文化出发,同时立足于哲学,从而展开真正的讨论与相互的学习。接着,复旦大学邓安庆教授的报告以“‘共存性正义’与‘个体性自由’:全球伦理的基础与目标”为题,对作为全球伦理之基础的“存在论正义”概念加以进一步的阐释与深化。邓安庆教授指出,在论文《全球伦理新构想》中,他通过对于“存在论正义”的阐发超越了政治哲学的 “全球正义”概念,并以此为基础证明了从存在之正义可以构成一种无中心、无强制的自然自由的全球性规范秩序;而本次发言将具体地论证如此这般自由的规范秩序通过何种有别于国内法的“立法程序”而成为普遍有效的规范机制,即从“世界公民”身份的“思想程序”,证明从不同文化的道德哲学中,可以通达一种普遍性的“共存性正义”,并以此作为全球伦理的基础。论证通过以下三个层次逐步展开:第一,全球伦理讨论需要从哲学上而不是宗教上为人类共存之正义奠基,因为唯有从存在论上对于正义的思辨出发,我们才能从各自所处的特殊文化和宗教的信念中抽身退出,进而使用公共理性思考世界之共存这一全球伦理的基础;第二,从多元文明的特殊伦理原则中可以推导出共同指向的人类“共存性正义”,因为若将地方性的伦理知识视为特定民族对于世界之存在机制的哲学探索,那么不同文明所确立的道德原则实则是对普遍有效的“共存性正义”观念的表达;第三,立足于“世界公民”的“共存性正义”秩序,才有保障“个体性自由”的充分发展,因为全球范围内的冲突从根本上是现代文明与前现代文明间的冲突;而对于个体自由的保障作为现代文明的基本要素,构成了全球文明正当性的基石和判准。只有在此标准之下,民族精神才得以实现世界化而进入世界历史,表达出特定民族对于全球伦理共存性正义的领会。因此,全球伦理的基础在于共存性正义,而目标依然是个体性自由的充分而自主地发展。随后,复旦大学汪行福教授的报告以“View from Nowhere——A Global Ethic for All Human Beings and Our Common Habitat”为题,分析了两种竞争性的全球伦理理论,提出了一种“不带有任何地方性色彩的全球伦理”的概念。首先,他指出了当前全球危机之下思考全球伦理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其次,他将汉斯·昆(Hans Küng)和希瑟·维多斯(Heather Widdows)的理论视为全球伦理考察中两种对立的研究取向。其中,汉斯·昆持有一种“最低限度的全球伦理观”,认为全球伦理的普遍原则可以从诸多主流宗教的基本共识中引出;而希瑟·维多斯则支持一种“综合的全球伦理观”,要求全球伦理将广泛的全球性问题纳入考虑,涵盖战争、移民和气候变化等诸多领域。然而,这两种立场都有其局限性。对此,汪行福教授指出全球伦理面临的核心挑战在于一方面在现代性的基础上说其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在现代文化和制度背景下展示其可行性。因此,全球伦理的基本原则和规范应该基于内格尔提出的“本然的视角”(view from nowhere),它要求个体放弃自己的特殊立场与主观意见,进而获得人类整体的普遍与客观视角。汪行福教授认为,“本然的视角”对全球伦理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为全球伦理的原则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其次,它可以作为区分全球性伦理问题与地方性伦理问题的标准。第三,它提供了对于全球秩序的批判性视角。在上半场会议的自由讨论部分,与会者基于以上三个报告的内容进行了讨论。Mandle教授对汪行福教授倡导的“本然的视角”提出了质疑。首先,Mandle教授指出自己在发言中强调了一种能够兼容具体经验的规范性理论的重要性,这恰恰批判了排除一切特殊性的中立视角。其次, “本然的视角”可以以另一种方式获得理解,正如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所说的那样,只有在承认个体的差异性与独立性的条件之下,我们才能做到不偏不倚。在这样的理解之下,“本然的视角”并非超然世外的立场,而是每个有理性的人可以在世界中采用的思维方式;以此为基础的伦理原则也并非源自对于特殊性的忽视或否认,而是将特殊性充分纳入其中的调节性原则。因而,如此被理解的“本然的视角”实质上是“view from everywhere”。 汪行福教授对Mandle的质疑进行了回应。他指出,“本然的视角”作为一种思维方式,要求人们以与主观偏好相疏离的方式思考,尝试将自己置于中立与公正的位置上,因而不能等同于“view from everywhere”。会议现场第二位来自欧洲某国的讨论人关注的问题是,我们需要全球伦理(global ethics)还是全球道德(global morality)?Mandle肯定了两者的区分,认为全球伦理研究需要将具体的伦理规范和更为基础性的道德原则区分开来,清晰地定义目前我们能够处理的工作。第三位讨论人是来自瑞典的哲学家Andreas Føllesdal教授,他一方面认为我们启动的全球伦理讨论十分必要和有意义,另一方面提出了一系列质疑性的问题:如果全球伦理是解决方案,那么它所针对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怎样的问题需要全球伦理来解决?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如气候问题,我们如何化解分歧?Mandle教授认为我们不能高估哲学家所能产生的直接政治影响,因为哲学所能做的充其量是逐渐地、慢慢地影响和塑造人们的背景、文化和取向。我们诚然应当对气候变化的原则和管理责任进行批判性反思,但是不能指望哲学家解决具体的伦理困境。汪行福教授就如何解决分歧、达成普遍原则进行了补充。他认为我们或可通过像在会议中进行的辩论来达成共识,或可汲取历史经验来寻求共识。第四位讨论者想进一步了解汪行福教授所言的“本然的视角”与中国的“天下”概念之间的相似之处。汪行福教授指出“天下”具有两重含义:第一,生活在不同地域的所有的人;第二,共同的规范性原则。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天下可以作为全球伦理的思想资源,因为它促使我们站在普遍性的高度思考伦理问题。但是,也要警惕一些中国学者对于“天下”概念的原教旨主义式的复兴,因为在这些学者看来,“天下”意味着一个具有中心化结构的世界帝国,国与国之间存在亲疏远近的等级关系,这是需要被否定的。在短暂的休息之后,下半场会议的专题报告部分又开始了。复旦大学王金林教授作了以“客观精神的‘萌芽’——全球伦理刍议”为题的报告,借用黑格尔思想资源重新审视了30年前通过的《世界伦理宣言》。报告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对全球伦理的讨论进行了历史性回顾,阐述了该宣言发表以来,全球伦理的理论框架及其概念遭遇的批评与挑战;第二,基于当下人类生存处境的重大变化,要求对全球伦理进行重新定性;第三,指出虽然《宣言》中的全球伦理概念可被定位为全球化时代社会性客观精神的“萌芽”,但它对概念中蕴含的历史性尚缺乏充分的自觉,未能真正突显全球尺度上人类迄今的道德文明之成就。若要有效地回应当今危机与挑战,全球伦理必须具有历史性、全球性、伦理性与方向性;第四,考察了全球伦理面临的三大主要障碍,即特殊主义、主权主义、发展主义并指出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对国家主权的尊重、对经济与技术发展的企求不应当损害全球伦理的

2024年8月5日,全球伦理圆桌会议暨第二届全球伦理国际论坛在意大利罗马大学顺利举行。论坛以“全球危机之下,如何重启全球伦理?”(Global Ethics: How to relaunch this discussion in the face of global crises?)为主题,作为第25届世界哲学大会“跨越边界的哲学”( Philosophy across Boundaries)圆桌会议之一。复旦大学全球伦理研究中心委员会成员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一同参与了讨论。与会者有复旦大学全球伦理研究中心主任邓安庆教授,复旦大学全球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王金林教授,复旦大学全球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汪行福教授,复旦大学全球伦理研究中心秘书长钱康青年副研究员,复旦大学全球伦理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成员、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Jon Mandle教授,特邀嘉宾同济大学张念教授,以及国内外对全球伦理怀以兴趣、抱以关切的来自诸多国家的学者们。会议分为上下两个半场,每个半场由专题研讨和自由讨论构成。
与会学者合影
在开场环节,复旦大学全球伦理中心秘书长钱康青年副研究员对复旦大学全球伦理研究中心(后文简称“中心”)的宗旨、性质与架构进行了介绍。他强调,中心旨在基于全球社会面临的伦理挑战,在哲学的层面上深入全球伦理的理论基础,探讨全球伦理的普遍原则与理性根据。鉴于过去数十年来全球伦理在推进和发展的过程中所遭遇到的阻力,中心的创立者们深刻意识到,要想在尊重世界文化多元性的情况下具体地确定某种全球性的伦理规则是及其困难的。因此中心更多的地将自己的定位视为是对全球伦理的理论基础进行深入反思,并且搭建能够促进世界各地的哲学家展开相互对话和交流的平台。经由去年在上海举办的第一届全球伦理国际会议,中心得到了国际学者的大力支持,其中包括来自世界哲学大会主席卢卡教授的认可,并受邀来到罗马参加世界哲学大会并主持全球伦理分会场。作为伦理学和哲学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和合作研究的平台,中心希望打破国界与学科的隔阂,将伦理议题拓展至全球范围,邀请更多学者重启全球伦理的讨论。
在上半场会议的专题研讨部分共有三位学者进行了主题报告。第一位报告人是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的Jon Mandle教授,他从哲学的方法论出发对全球伦理的讨论进行了反思。他指出,目前存在两种广为接受的伦理学研究方式:一种可以被称为道德人类学路径,采取这一路径的学者重视实践形态与道德原则的多样性,他们试图对世界各地不同社会、不同社区、不同文化中的道德进行描述;另一种则被归于规范理论,采取这一路径的学者旨在确立合理的道德原则,认为普遍的道德原则可以应用于不同的文化群体,乃至推广至全球范围。但是,这两种研究路径都存在理论上的风险:道德人类学无法从现存的事实出发推导出道德性的规范原则,因而反有可能为特定社会中存在的不公辩护;而规范理论家则忽视了不同社会、文化和群体分享着彼此差异与多样的价值,为了高度抽象的概念与理论牺牲了生活经验的复杂性。Mandle教授指出,道德人类学家和规范理论家需要相互学习,尤其是对于采取后一路径而哲学家而言,应当基于人类学对现实社会的经验考察,以使得诸如自由与平等的抽象概念获得具体的内容。在会议结束后,Mandle教授接受了中的采访,并进一步补充了自己的观点:首先,Mandle教授肯定了1993年《全球伦理宣言》的积极价值。他认为,《宣言》代表着建立一个共享的、全球性的伦理规范的努力,这有助于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相互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信任和熟悉度。尽管在过去、现在和将来,想要形成这样一种全球性的共识都不可避免地会早遇到各种冲突和分歧,但至少大家可以在一种共同推进的努力中探索可以分享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的领域。换言之,即便这种探索无法即刻产生实际的影响,但从长远的视角看,一定是能够对全球伦理的工作产生助益的。接着,Mandle教授指出了重建全球伦理的两重挑战:第一,理论困难,即在承认多样性的前提之下如何构建共同价值观与共同的规范原则;第二,现实障碍,即由于当下广泛存在的信任危机,跨国联结变得困难。哲学家更多考虑的是第一点,也就是探寻普遍的规范原则。然而,单纯对不同的观点进行分类,然后试图找到共识或重叠是不可行的,因为全球性的伦理规范需要被建构而非单纯地被发现。换言之,Mandle教授并不认为有一个全球性的道德规范等待被发现,全球伦理研究的方法应该是一种能够包容和尊重多元价值的哲学重构。所以,解决理论困境的正确途径是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促进不同传统之间的对话。在这个意义上,建构全球伦理的关键在于在统一中保持多样性,在以相互尊重为前提的对话中看到其他观点的合法性,一方面坚持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在与他人的互动中的跨越自身主观性的限制。随后,Mandle教授强调共同原则的合法性在于理性的公共使用,即承认不同观点的平等合法性,并允许这些彼此相异的特定视角与价值被纳入共享视角的构建中。在这种建构中,类似于罗尔斯所提出的“理性的公共使用”是至关重要的。最后,他对复旦大学全球伦理研究中心表达了赞许,认为中心使得世界各地的学者们可以从不同的文化出发,同时立足于哲学,从而展开真正的讨论与相互的学习。
接着,复旦大学邓安庆教授的报告以“‘共存性正义’与‘个体性自由’:全球伦理的基础与目标”为题,对作为全球伦理之基础的“存在论正义”概念加以进一步的阐释与深化。邓安庆教授指出,在论文《全球伦理新构想》中,他通过对于“存在论正义”的阐发超越了政治哲学的 “全球正义”概念,并以此为基础证明了从存在之正义可以构成一种无中心、无强制的自然自由的全球性规范秩序;而本次发言将具体地论证如此这般自由的规范秩序通过何种有别于国内法的“立法程序”而成为普遍有效的规范机制,即从“世界公民”身份的“思想程序”,证明从不同文化的道德哲学中,可以通达一种普遍性的“共存性正义”,并以此作为全球伦理的基础。论证通过以下三个层次逐步展开:第一,全球伦理讨论需要从哲学上而不是宗教上为人类共存之正义奠基,因为唯有从存在论上对于正义的思辨出发,我们才能从各自所处的特殊文化和宗教的信念中抽身退出,进而使用公共理性思考世界之共存这一全球伦理的基础;第二,从多元文明的特殊伦理原则中可以推导出共同指向的人类“共存性正义”,因为若将地方性的伦理知识视为特定民族对于世界之存在机制的哲学探索,那么不同文明所确立的道德原则实则是对普遍有效的“共存性正义”观念的表达;第三,立足于“世界公民”的“共存性正义”秩序,才有保障“个体性自由”的充分发展,因为全球范围内的冲突从根本上是现代文明与前现代文明间的冲突;而对于个体自由的保障作为现代文明的基本要素,构成了全球文明正当性的基石和判准。只有在此标准之下,民族精神才得以实现世界化而进入世界历史,表达出特定民族对于全球伦理共存性正义的领会。因此,全球伦理的基础在于共存性正义,而目标依然是个体性自由的充分而自主地发展。
随后,复旦大学汪行福教授的报告以“View from Nowhere——A Global Ethic for All Human Beings and Our Common Habitat”为题,分析了两种竞争性的全球伦理理论,提出了一种“不带有任何地方性色彩的全球伦理”的概念。首先,他指出了当前全球危机之下思考全球伦理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其次,他将汉斯·昆(Hans Küng)和希瑟·维多斯(Heather Widdows)的理论视为全球伦理考察中两种对立的研究取向。其中,汉斯·昆持有一种“最低限度的全球伦理观”,认为全球伦理的普遍原则可以从诸多主流宗教的基本共识中引出;而希瑟·维多斯则支持一种“综合的全球伦理观”,要求全球伦理将广泛的全球性问题纳入考虑,涵盖战争、移民和气候变化等诸多领域。然而,这两种立场都有其局限性。对此,汪行福教授指出全球伦理面临的核心挑战在于一方面在现代性的基础上说其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在现代文化和制度背景下展示其可行性。因此,全球伦理的基本原则和规范应该基于内格尔提出的“本然的视角”(view from nowhere),它要求个体放弃自己的特殊立场与主观意见,进而获得人类整体的普遍与客观视角。汪行福教授认为,“本然的视角”对全球伦理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为全球伦理的原则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其次,它可以作为区分全球性伦理问题与地方性伦理问题的标准。第三,它提供了对于全球秩序的批判性视角。
在上半场会议的自由讨论部分,与会者基于以上三个报告的内容进行了讨论。Mandle教授对汪行福教授倡导的“本然的视角”提出了质疑。首先,Mandle教授指出自己在发言中强调了一种能够兼容具体经验的规范性理论的重要性,这恰恰批判了排除一切特殊性的中立视角。其次, “本然的视角”可以以另一种方式获得理解,正如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所说的那样,只有在承认个体的差异性与独立性的条件之下,我们才能做到不偏不倚。在这样的理解之下,“本然的视角”并非超然世外的立场,而是每个有理性的人可以在世界中采用的思维方式;以此为基础的伦理原则也并非源自对于特殊性的忽视或否认,而是将特殊性充分纳入其中的调节性原则。因而,如此被理解的“本然的视角”实质上是“view from everywhere”。 汪行福教授对Mandle的质疑进行了回应。他指出,“本然的视角”作为一种思维方式,要求人们以与主观偏好相疏离的方式思考,尝试将自己置于中立与公正的位置上,因而不能等同于“view from everywhere”。
会议现场
第二位来自欧洲某国的讨论人关注的问题是,我们需要全球伦理(global ethics)还是全球道德(global morality)?Mandle肯定了两者的区分,认为全球伦理研究需要将具体的伦理规范和更为基础性的道德原则区分开来,清晰地定义目前我们能够处理的工作。
第三位讨论人是来自瑞典的哲学家Andreas Føllesdal教授,他一方面认为我们启动的全球伦理讨论十分必要和有意义,另一方面提出了一系列质疑性的问题:如果全球伦理是解决方案,那么它所针对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怎样的问题需要全球伦理来解决?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如气候问题,我们如何化解分歧?Mandle教授认为我们不能高估哲学家所能产生的直接政治影响,因为哲学所能做的充其量是逐渐地、慢慢地影响和塑造人们的背景、文化和取向。我们诚然应当对气候变化的原则和管理责任进行批判性反思,但是不能指望哲学家解决具体的伦理困境。汪行福教授就如何解决分歧、达成普遍原则进行了补充。他认为我们或可通过像在会议中进行的辩论来达成共识,或可汲取历史经验来寻求共识。
第四位讨论者想进一步了解汪行福教授所言的“本然的视角”与中国的“天下”概念之间的相似之处。汪行福教授指出“天下”具有两重含义:第一,生活在不同地域的所有的人;第二,共同的规范性原则。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天下可以作为全球伦理的思想资源,因为它促使我们站在普遍性的高度思考伦理问题。但是,也要警惕一些中国学者对于“天下”概念的原教旨主义式的复兴,因为在这些学者看来,“天下”意味着一个具有中心化结构的世界帝国,国与国之间存在亲疏远近的等级关系,这是需要被否定的。
在短暂的休息之后,下半场会议的专题报告部分又开始了。复旦大学王金林教授作了以“客观精神的‘萌芽’——全球伦理刍议”为题的报告,借用黑格尔思想资源重新审视了30年前通过的《世界伦理宣言》。报告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对全球伦理的讨论进行了历史性回顾,阐述了该宣言发表以来,全球伦理的理论框架及其概念遭遇的批评与挑战;第二,基于当下人类生存处境的重大变化,要求对全球伦理进行重新定性;第三,指出虽然《宣言》中的全球伦理概念可被定位为全球化时代社会性客观精神的“萌芽”,但它对概念中蕴含的历史性尚缺乏充分的自觉,未能真正突显全球尺度上人类迄今的道德文明之成就。若要有效地回应当今危机与挑战,全球伦理必须具有历史性、全球性、伦理性与方向性;第四,考察了全球伦理面临的三大主要障碍,即特殊主义、主权主义、发展主义并指出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对国家主权的尊重、对经济与技术发展的企求不应当损害全球伦理的基本原则。
最后,同济大学人文学院的张念教授从女性主义视角对全球伦理进行了反思。张教授首先从“什么是多样性?”出发,指出我们通常在文化与政治语境下考察“多样性”,这意味着对于“多样性”的讨论被限制在理性主义的哲学范式之下。然而,如果从感性哲学的角度出发,“多样性”则意味着感性的丰富与具体。那么,对于感性主体而言,我们如何确立普遍原则?理性的逻辑对于解决伦理冲突而言是否充分?感性的逻辑对于伦理而言意味着什么?或许女权主义实践已经表明了这种可能性,我们应该学会使用我们的感觉,去爱一个具体的他人,并通过他们的面容、声音和姿势中与他们建立联系、寻求理解,因而从女性主义去发展情感伦理和关怀伦理,或者还是一个比理性主义更有效的全球伦理进路。
在下半场会议的自由讨论部分,与会者基于以上两个报告的内容进行了讨论。第一位发言人现为来自波兰的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哲学系的在读博士生,她指出跨语言的沟通在全球伦理研究中具有重要性。她认为只有对全球伦理中的核心概念与关键著作进行更多的翻译,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才能顺利实现。因为翻译不仅仅是直译或试图表达意思并传达它们,而是发生于不同文化视野之间的思想碰撞。第二位发言人是一位来自罗马的音乐家,他认为语言系统的多样性反而是全球伦理讨论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跨文化交流并非增加了沟通上的困难,而是增添了讨论的丰富性。第三位发言者是复旦大学的在读博士生,她指出如果我们仅仅使用英语讨论全球伦理,那么不可避免地产生概念上的模糊。
来自奥斯陆大学的Føllesdal教授进一步强调了重建全球伦理的关键,在于从不同的文化传统中获取思想资源,因为每个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特定的视阈与问题,哲学家要做的是理解这些差异,以此为基础展开学习与批判。比如,一些西方哲学传统确实非常认真地对待全球范围内的道德的深刻分歧,但这并非考察问题的唯一视角。孙向晨教授对于中国家庭观念的讨论就能让我们了解到中国哲学中的共同体视角,而西方哲学家大多没有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这种文化差异是我们需要更多思考的领域。
来自美国天普大学的一位博士后从公共卫生领域出发对全球伦理进行了反思。他对全球伦理的兴趣来自新冠疫情引发的全球正义和健康正义的问题,但是,他强调,全球伦理的价值并不在于切实地解决我们当下面临的全球问题,而在于提供一般性的原则,使全球化进程中的所有参与者得以在遵循这些原则的基础之上,提出切实可行的政治解决方案。
来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一位助理研究员基于自身的研究背景表达了对于全球伦理的看法。他认为,公共性是全球伦理的核心特征,因为全球伦理实质上旨在为全人类提供一种公认的对世界、对生活的态度,为国际合作与交流提供基础性共识。而这样的理论目标为诸多哲学流派所分享,他所研究的印度宗教哲学中的吠檀多学派,其核心思想可以被概括为人和世界终极本源在根本上的一致性。在这个意义上,它探讨了存在于不同个体之间相同的根本与基础,为寻求共识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思考路径。
复旦大学全球伦理研究中心主任邓安庆教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总结。邓安庆教授首先指出了本次会议的要旨,在于以哲学的路径开启对于全球伦理讨论,因为以理性为基础是全球伦理的题中之义。30年前的全球伦理探索试图从主流宗教共享的道德原则引出全球伦理原则,但是每个宗教过于强烈地信仰自身宗教的绝对神明以此来为伦理与道德立法,使得它很难突破信仰的边界,跨越文化的差异,以产生跨越宗教和政治的世界伦理共识。唯有哲学才能凝聚世界理性的力量,让不同观点的对话得以可能;只有将各民族理性精神中体现的道德原则提取出来,通过罗尔斯式的道德直觉,才能获得全球人类共同生存的规范秩序建构的全球视野。正如他在报告中将“共存性正义”与“个体性自由”作为全球伦理的两大关键要素,前者意味着全球伦理必须跨越本民族的边界,以世界精神为指向,找到本民族伦理原则与全人类共通共享的共同价值,将共存性正义作为全球伦理的基石与单个民族在世界上获得立足的道德条件;后者意味着使现代性所要求的个体自由落实于每个世界公民与单个民族国家之上,不仅在观念上建构起全球伦理共识,还要以自由自愿为基础,凭借有效的具体机制来规范自由自主的地方性行动。随后,邓安庆教授将会议的圆满成功归于两点:第一,启动全球伦理的讨论与世界哲学大会“跨越边界”的努力高度一致,因为全球伦理的讨论必然具有引导学者超越所属民族与国家的世界伦理立场,一方面冲击本民族伦理的边界,另一方面挖掘出特定文化与民族所具有“跨越边界”的普遍主义天赋。第二,将超越单个民族的公共理性作为讨论全球伦理的基点,这一基本路径引来了国际学者的广泛认可,吸引他们积极参与讨论。这也是本次会议比第一届全球伦理国际论坛更进一步的地方,学者们开始有意识地从方法论的角度展开讨论,从哲学的角度分析不同文明建立伦理原则的理性基础。
你的反应是什么?